据光明网报道:4月13日,2022年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四川泸州举行。贾平凹的《秦岭记》和庞贝的《乌江引》获长篇小说奖;关仁山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和韩青辰的长篇小说《中国少年》获特别奖;王蒙的《从前的初恋》和肖勤的《隐秘的船》获中篇小说奖;盛可以的《女猫》和陈刚的《城防图》获短篇小说奖;梁衡的《风沙行》和彭学明的《马王溪光景》获散文奖;徐刚的《自然笔记》和陈国栋的《地球印记》获非虚构作品奖;栗鹿和康岩分别凭借中篇小说《空蛹》和报告文学《燃灯者李大钊》获新人奖;马嘶的《追白云》和秦立彦的《凝视》获诗歌奖;《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编辑总监艾瑞克·阿布汉森和韩文版《灯光》编辑总监金泰成、译审金京善获翻译贡献奖。
人民文学奖是《人民文学》的年度奖,每年颁发一次,评选范围为该年度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发的优秀作品,以及该年度为《人民文学》中文版和外文版作出巨大贡献的作家与专家。本次评选围绕2022年度《人民文学》中文版和各语种外文版展开。
获得2022人民文学奖的这些作品中,我曾经阅读过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岭记》、庞贝的长篇小说《乌江引》、陈国栋的非虚构作品《地球印记》,并且还撰写拙评,并且分别在《河北日报》《北京日报》《文学报》发表。全文如下:
当前很多小说,在人物刻画和故事讲述方面绞尽脑汁,但是对于自然场景的再现则轻描淡写,所以有人感叹,自然场景是什么时候在当代小说中退场的?淡化自然场景的描写,不仅是小说创作的遗憾,深层次讲就是自然认知的迷失。贾平凹的长篇笔记小说《秦岭记》,其小说之名就开宗明义,将自然场景推到了叙事的前台,山川河流草木飞鸟走兽,成为小说文本的最大看点。重返自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时代赋予文学的新使命,也是小说创作的新机遇和新路向。
从事文学创作已近50年的贾平凹,是从陕南农村走出来的作家,从小对自然万物充满好奇。他青少年生活的地域,也算是秦岭的一部分。他的创作中,对自然都有精彩细腻的表达,如《浮躁》《商州》《高老庄》《怀念狼》《古炉》《山本》《秦腔》等等。而《秦岭记》这部小说,是作家对自然的集中和深度的思考,是文学自然观的一次整体亮相。
《秦岭记》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讲述秦岭中人与自然的近60个故事,其中有山川里隐藏着的万物生灵,有河流里流淌着的生命低语,还有万千沟坎褶皱里生动的物事、人事、史事。小说中,既写秦岭的天文地理、村落山民、鸟兽虫鱼,也写花草树木和人生之悟。阅读中不难看出,这部小说有《山海经》《聊斋志异》等中国传统文学的基因,其境界开阔深远、笔法摇曳多姿。
对于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言,创作中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和地域因素,这些因素让作品最后形成独特的气质和面相。2017年创作长篇小说《山本》时,贾平凹说秦岭是“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2021年创作《秦岭记》收官之时,他反倒不知如何去描述秦岭,“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写秦岭,写它历史的光荣和苦难,写它现实的振兴和忧患,写它山水草木和飞禽走兽的形胜,写它儒释道加红色革命的精神。如果概括一句话,那就是:秦岭和秦岭里的我。”不难看出,作家对于秦岭的深情,藏在骨子里、流淌在血脉中。
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贾平凹所写的故事,皆发生于文学地理意义上之秦岭南北,而中国大历史之重要事件,亦大多发生于此。在秦岭里行走,贾平凹能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他的笔端对准秦岭,既写自然的秦岭,也写人文的秦岭,有“双向奔赴”之感。自然的秦岭绿水青山、物产丰富,就是一座大型的宝藏。对自然秦岭的文学呈现,他当然不会直奔主题,更不会简单表达热爱之情,而是如数家珍,对秦岭风物进行“记录”。这种记录,是发挥文学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加之直面现实的反思精神。
《秦岭记》的每一行字,感觉都是有生机的、奔腾的,这样的小说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快读,而是要安静下来慢慢品。小说开篇,写到秦岭有一条倒流河,河流一般是由西往东流淌,而这条河由东向西。倒流河边有一座白乌山,山是一块整石形成,山上只生长楷树和模树。如此特殊的河和山,其实是为整部小说定调:秦岭的一切是不凡的,自然万物的各种故事在这里轮番上演。小说中写到,有一棵古银杏树,原本被老人照看得挺好的,可一个商人绞尽脑汁雇人砍掉,可是在运输途中,一系列离奇的遭遇让商人不寒而栗,他悟出一个道理:古树虽不会说话,但也有生命的气场,糟蹋古树必遭天谴。小说中没有多余的感慨和议论,在叙事中表达一种质朴的自然观:人与自然万物其实就是生命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平衡若破坏了,就会遭到自然的惩戒。
《秦岭记》对于动物有精彩的描写。在秦岭南坡,一个接一个的村落,质朴的山民一代又一代在此安居,这里常有各种动物出没。小说中对动物的描写,想象丰富、读来让人脑洞大开:“他面前是一只鹅,鹅在叫着自己的名字……一头猪前腿搭在圈墙上,‘哼哼唧唧’在笑。”拟人的手法,把动物写得惟妙惟肖,尽管显得夸张,但这山林的语境中恰到好处。在贾平凹的眼里,树也好、动物也罢,都通人性,都能和人交流。这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看出,人在自然万物面前,根本就没有什么优越感,人就是自然物种中的一分子。
《秦岭记》呈现出的自然与人,就如同一个魔幻而传奇的万花筒:能听懂人话的忠犬;高僧进入便会流出泉水的山洞;人抱着哭,叶子就会一起流眼泪的皂角树;可以进入别人梦境的小职员……小说中,类似这样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人、动物、植物比比皆是。在现实的自然世界里,自然万物看上去是平凡的、不足为奇的,而在贾平凹的笔下,自然界一切生命的进场和退场,都自有安排。
《秦岭记》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稳健,充分彰显一位作家老到的文学内功。写好中国文字的每一个句子,是贾平凹的座右铭。“不论是人是兽,是花木,是庄稼,为人就把人做好,为兽就把兽做好,为花木就开枝散叶,把花开艳,为庄稼就把苗秆子长壮,尽量结出长穗,颗粒饱满。”这形象生动的比喻,值得所有作家去仔细揣摩。
贾平凹不是专门的自然文学作家,但是自然世界在《秦岭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若一个人不经常在自然中行走,对自然万物不够友善,就不会写出这样接地气、沾露珠的力作。笔者无意给贾平凹和这部小说贴上自然文学的标签,可是他书写自然的情怀和智慧,足以令人折服。

红军长征途中,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长期以来,围绕这一主题,文学艺术界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长征就如同文艺创作的巨大“矿藏”,可以用不同方式、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开掘”。长篇小说《乌江引》丰富了红军长征主题的文学书写,拓展了军事文艺创作的空间。
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庞贝,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在出版这部小说之前,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无尽藏》《独角兽》,以及多部戏剧和电影剧本。庞贝早年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基于这样的职业背景,在历史题材的《无尽藏》和科幻题材的《独角兽》之后,创作这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对于庞贝而言,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乌江引》这部文学分量十足的军事题材作品,意味着庞贝在文学之旅的初心与回归,是文学创作中的一次长途远征和翻山越岭。
众所周知,在军事斗争中,情报系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假如无法准确掌握并破解敌军的真实情报,红军长征就会非常被动。如毛泽东同志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所以能一次次成功避开敌军的围追堵截,和红军破译敌军密电有直接关系。红军长征中的“信息战”“情报战”,和正面战场一样,同样惊心动魄,极为考验红军队伍的智慧。长篇小说《乌江引》的重点笔墨,直指无形之中的“秘密战”。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经过两年、八省、两万五千里行程的战略大转移,红军三大主力粉碎了国民党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而在长征史诗广为人知的史实之外,还存在着鲜为人知的传奇:以“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为破译主力的中革军委二局,是“一支鲜为人知的秘密力量”。他们利用早期无线通讯技术侦收的敌台信号,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情报,为红军一次又一次突破重围、绝处逢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国民党军对红军的情报却一无所获,这是人类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情报战例。
长篇小说《乌江引》以这段真实的历史为创作背景,以大量解密档案及“破译三杰”后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在客观史实基础上,辅以文学的想象。小说的主体故事发生在红军主力1935年1月初突破乌江、3月底南渡乌江之间,其间有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捷和四渡赤水等大事件,这也是长征途中最为关键、最富戏剧性的辉煌篇章。
《乌江引》既有历史的现场感、纵深感,又有文学的审美感和语言艺术的独特魅力。小说在谋篇布局上,没有按照“起承转合”这种传统的叙事模式展开,而是另辟蹊径,小说分为“速写”和“侧影”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军委二局匿名者的战地笔记,第二部分是今人对这段秘史的艰难寻访。小说用虚实相伴的复调笔法触摸历史、还原历史、书写历史,还巧妙地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整个二十世纪革命战争串联起来。这无疑考验一个小说家的叙事功力。小说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在两万五千里情报战的“速写”式叙事中,在后人对记忆碎片的寻觅和回忆之中,逐渐显现出一个无名者的“侧影”。“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还活着。”
由此,《乌江引》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思想意蕴:一个有关记忆与身份的现代主题。基于匠心独运的结构形式和故事、语言、节奏诸方面所呈现的质感,小说实现了非虚构史实和虚构性描写的完美融合,史学与文学交会,虚实相生,呈现的是一个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叙事文本。全书既有“秘密战”的惊心动魄,也有正面战场的恢弘壮阔。这是热血和勇气的展现,也是青春和生命的祭奠。在时间深处,在记忆深处,依然有这一代人不灭的身影,那是他们的信念、坚卓和智慧。
鲜为人知的是,红军对敌军的密码破译工作,并非始于长征,而是始于二次反围剿,“密码之父”曾希圣短时间内组建了一支精明强干的密电队伍,且很快在技术上达到当时中国军事密码破译的巅峰。可以这么讲,如果说红军长征是夜中向前跋涉,那么中革军委二局是“灯笼”,是红军走向胜利的有力撒手锏。一般来讲,对于情报战题材的小说创作,很容易陷入各种技术的繁复表述,从而让作品显得头绪不清,主题弱化。但《乌江引》则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没有因为讲述的是密码破译的技术工作,就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智慧和战略决策还原成纯技术,而是巧妙地处理了密电破译和战略决策的关系,在不可辩驳的历史真实中展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智慧和胆略。
有关红军长征情报战的长篇小说作品,在《乌江引》出版之前,文坛是一片空白。而这部小说的问世,填补了这一题材的真空。作为第一部以中革军委二局为书写对象的长篇小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小说具备揭秘历史、发掘以“破译三杰”为代表的无名英雄功业的价值。正是小说基于真实史料为底色、用文学的方式进行表述,使得这部小说不仅新意不断、意蕴丰满,也是对伟大长征精神的深情礼赞。
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其小说之名是颇为讲究的,《乌江引》就是如此。这部小说的“引”,本身就有“弓”字的象形,弓有弓背和弓弦。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之后又折道云南,北渡金沙江,走的是“弓背路”(曲线)。当时,红军中某些高级指挥员,不知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们如此决策的依据,就是由于军委二局破译的敌军情报,他们主张走“弓弦路”(直线)。因此,“引”字是长征路线图的形象呈现。
以往书写情报、破译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往往强调“隐”和“密”,使得小说氛围扑朔迷离,有时让读者不知所云。但《乌江引》站在正史的正面,展现的是红军队伍的智慧与力量。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小说还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无形地呈现在字里行间,妥善处理好了虚构和非虚构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既有一泻千里的气势,又有千回百转的情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乌江引》是当前长征主题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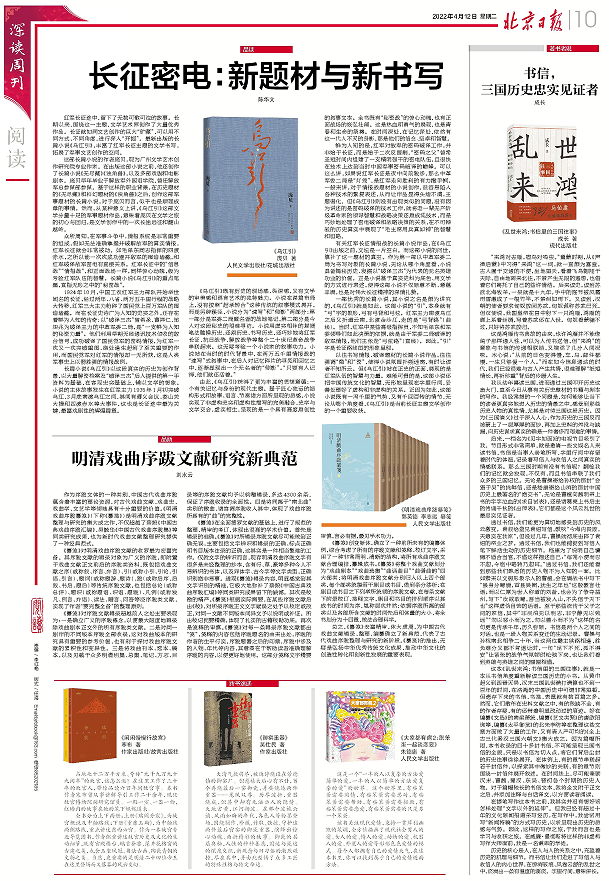
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主题的文学书写,当前成燎原之势,相关文学佳作层出不穷。针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文学叙事,在主题、内容和文体方面,有多种路径选择。《人民文学》杂志2022年第八期,头题发表3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地球印记》,作品以温情的笔墨,讲述了我国建设地质公园的历程、专家学者的付出以及地质公园在美丽中国建设中的价值意蕴。作为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刊发自然生态主题作品,充分表明新时代自然文学的创作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某种程度上讲,这会激发更多人投入到自然生态文学的创作之中。
《地球印记》的作者陈国栋,现为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主席,他不仅有在自然资源系统长期从事领导和科研工作的经历,这些年来还行走在山河之间,发表一系列自然生态主题的报告文学力作。《地球印记》以现场感、代入感和沉浸式的特点,将地质公园的诸多故事娓娓道来。行文中,“我”的采访贯穿始终,“我”的情绪起伏和波动,推动着叙事向前行进。对于地质公园的故事讲述,作者并没有泛泛而谈,而是依托于克什克腾、阿尔山、泰山这三个世界地质公园,在观察和行走中进行重点呈现。
地质公园是一种“大地景观”,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厚礼。为地质公园专门文学“画像”,《地球印记》还是第一次。作品开篇写道:“人类把亿万年来地球演化过程中留存下来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遗迹,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源,建立诸如自然保护区、地质遗迹保护区、地质公园、湿地公园、国家公园等方式,将其加以保护利用,这是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相信自然,建设美丽地球家园的明智选择。”这一段话简短有力地表明,以地质公园为代表的“大地景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深远寓意,作品在接下来的行文中,基本也是在这个认知框架下进行。
《地球印记》作为一部具有地学底色的报告文学作品,必须对地质公园进行整体“素描”,这有助于我们从感性上有一个形象的了解。简单地讲,地质公园是在地质遗迹和地质景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自然公园,这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目前有41个世界地质公园、277个国家地质公园、400个省级地质公园,地质公园“犹如大地上的一片片绿叶、一朵朵繁花,点缀着美丽的山河大地”。从地学专业的维度看,不同的地质公园其地质地貌各有千秋,但无论通过哪个地质公园,都可以探访地球演化的奥秘,地质公园如同一把时光之匙,能破解世间万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迷踪。从社会的维度看,建设地质公园是在不改变资源的位置和属性的前提下,保护好自然资源,通过发展旅游带动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建设地质公园,是在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光鲜与精彩的背后,往往是艰辛和曲折。地质公园的规划和建设和其他事业一样,需要有人默默付出。《地球印记》中,对专家学者这一群体进行了刻画。内蒙古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建设过程中,大学教授田明中20年来过40次,他和当地的人们以及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任何一处地质遗迹,他都如数家珍。人们亲切地喊他“田大叔”。为了大兴安岭丛林中的阿尔山世界地质公园规划,专家学者们深入丛林进行野外勘察,很多困难接踵而至。如遇到湍急而冰冷的河水,必须卷起裤腿蹚过去;肚子饿了、口渴了,啃一块坚硬的面包、喝一口冰冷的水;为了避免蜱虫侵袭,需小心谨慎做好防护;为了在丛林中不迷失方向,必须跟着定位导航向前跋涉。其中,一个年轻的女专家,在野外测量时不慎落水,但她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好数据记录和测量装备……《地球印记》把这些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记录了下来,让我们重新认识平凡、可敬、可亲的地质公园工作者们。其实,全国类似这样的专家学者群体还有很多,他们心怀家国、情系自然,真正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彰显了崇高的胸怀和品格。
《地球印记》告诉我们,当人类关爱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的。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人类生活环境公园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趋势,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目标。
这部以地质公园为“主角”的报告文学,拓展了报告文学写作的主题空间,提升了自然生态文学的内涵与厚度。通读作品,给笔者带来三点启示:一是报告文学要为时代立传。我们这个时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社会和人民关注的焦点,也应该是报告文学关注的焦点,从地质公园到国家公园,都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议题,把大地故事书写好,把内在的精神展示好,是时代赋予报告文学的重任。二是自然生态文学要“开疆拓土”。自然生态文学写作当前备受各方关注,同时也要冷静地看到,大地故事和自然故事,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一座山脉、一条河流、一片森林的粗浅呈现,而是要在美丽中国建设的宏阔视野下,发掘和开拓自然生态写作的新题材与新方向,如对地质公园文学“画像”,就是一种新探索。可也要看到,《地球印记》只是起笔,这个题材的写作需要不断丰富和深入。三是讲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故事。无论是通过报告文学、小说还是散文,讲述人与自然的故事都有无限的可能性,人与自然的文学书写不能厚此薄彼,要两者兼顾,既要呈现人在保护自然、保护绿色中的作为和智慧,也要展现大自然的五彩缤纷、丰满充盈,让自然真正“动”起来,赋予灵秀之美。唯有如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学故事才会生动走心,不断地感染人、影响人。

《文学报》版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