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1年,我在曲阜读大一,看到学校团委有个征文,我在宿舍用信纸仿写一篇《秋之倒影》,不想却获得三等奖。这,如果也算发表的话,应该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字了。
遥想这次获奖,如果当初没有投稿呢?会不会还能够激发自己的写作兴趣,这都有些不得而知。好的是,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我在阅读到写作的道路上,逐渐开启着新希望。
从2001年到2021年,整整20年,浸润在文字的世界里,尽管没有成就什么伟业,却也算得上自得其乐;尽管没有赚多少稿费,但也偶尔能收到不少稿费,这也算是对一个文字爱好者的不舍放弃的馈赠了吧!
如今,我有几个公众号,且保留了留言功能,不希望都放弃,就继续更新下来了。『言立方』定位是『故乡。故人。故事。』『时评社』定位是『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些号,粉丝不多,但却不舍对其爱与自由。偶有感触,便义不容辞地写下来,作为总结,作为记录。
未来,或许还有更多新的载体吧。姑且等着来,来了,就接住。唯一不变的,大概就是写,坚定不移地写下去的苦苦坚持。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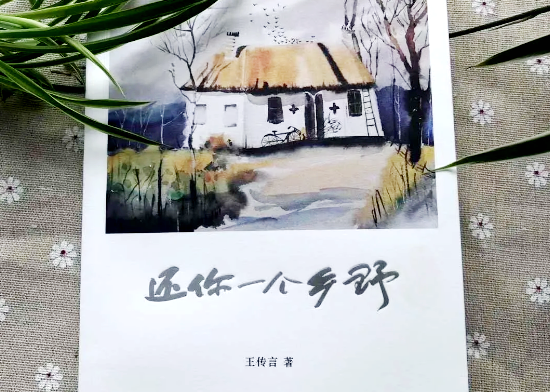
2020年5月,《还你一个乡野》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拿到这本真正属于自己的书,莫名地喜极而泣。作为自己文字的总结,作为对故乡情结的回望,作为一个文字挚爱者的情怀,能够有本署名书,算得上是夙愿。如今,却从梦想变成了现实。对一位从乡村走到城市的孩子,多少是有些欣慰的。
回首这本书的出炉,也算得上曲折。2018年,为即请高中同桌兼好友尹冬民题写书名,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他已成绩斐然。收到题字后,默默装裱收藏起来,等待出版时机的到来,不曾想到,这一等就是两年之久。好的是,题字终于用上了,同桌的字也终于印刷在自己的书上。
在书籍内容的整理上,我将曾经发布在公众号上的文字进行系统收集分类,整理成“乡人篇”、“乡风篇”和“乡物篇”。每篇的标题,都使用了四个字的格式。比如“三舅来兮”、“大嫂如斯”、“爆米花来”、“洋火枪响”。最终印刷出来的统一让读者看上去觉得有些气势在内,这便是我曾经的初衷。若是字数不一,就觉得太随意。
书出来后,我按部就班地去读书会和书店进行分享,也将书邮寄给曾经的同学,曾经提携过自己的人,曾经的文友,希望他们能够和我一起分享新书的喜悦。在分享中,我渐渐地发现,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一个爱好,多少是有些难度的。尤其是当势利眼的人抛来鄙视的目光,他们拿着世俗的评价机制,说着“不就是出了本书,又赚不了多少钱”的风凉话的时候,我多少有些失落感。
或许,实现夙愿和经济价值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均衡的时刻。当我再次回望《还你一个乡野》这本书的时候,想起的不仅是书里的内容,更是自己触发写作的原点和这么多年以来写作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转折点,不胜唏嘘。
三
1983年出生的我,小小山村里,童年没有任何课外书相伴,所学不过教科书。当翻箱倒柜找寻后,倒是发现几本《红旗》杂志,那是母亲用来夹鞋样的,不仅缺页严重,也早已泛黄。
尽管如此,还是将里面残缺不全的内容逐一阅读下去,也对所有带字的纸张有天然的敬畏感,不能让它们在我眼前消失,消失之前得静静地看上一遍,才算不浪费。
偶尔发现个《农村大众》的报纸片段,也认真地读完上面的字才肯丢掉;父亲的《电工手册》也一度成为我阅读的篇章,但太枯燥无味,那些横七竖八的线路图,搞得年少的我晕头转向。
对阅读的痴迷,直到大学后变成了现实。每个人的阅读,大概都是有所倾向的吧,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按照内心阅读即可。在图书馆里,我对李敖的书痴迷不已,将馆藏的《李敖大全集》共40本悉数阅读完毕。阅读又是有连锁反应的,即你阅读一本书,会从书的内容延伸到另外一本书,从此一本接着一本,根本停不下来。
从李敖的书里又开始读胡适的书,又开始喜欢上民国那个时代,将梁启超、徐志摩、沈从文、林徽因、金岳霖、梁思成等人的事迹逐一看一遍,顿时觉得心理上已经提升了一个档次,灵魂上与他们有些许的契合了。这当然是一种文人气质的惺惺相惜,也算是内心希望成为的样子的投射吧!
宽松的校园环境,丰富的图书资源,充分的课余时间。正是这些阅读体验,让我觉得只是阅读输入远远不够,还需要写作输出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迸发了要写点什么的念想,但也只是想想而已,没有将其诉诸行动。
四
有机会,就要尝试;能碰到志同道合的人,更是一种幸运了。这个转折发生在研究生阶段,那正是博客刚刚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刻。但我自己并不知道。所以,真正的写作,认真的写作,如果真的要算起的话,还要追溯到2006年2月,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在同学的推荐下,注册了自己的搜狐博客,开启了一个更新的时代。
博客属于开放平台,每个人都可以注册发布自己想写的内容,博客也是一个互动的渠道。在博客时代里,几乎每天都能够发布点滴的记录,无论字数多少,却都是来自于自己的真情实感,像日记,像随感,留下了属于那些时代的印记,也让自己的写作夙愿获得了展示。因为也就是在博客的时代里,我的第一篇文字被报纸刊发了。
那是2006年9月的一天,我在图书馆阅览室看到苏州当地报纸《姑苏晚报》上有个博客征文活动,回到宿舍后就将自己的一篇博文《浪漫靠后》投递到指定邮箱。没想到的是竟然给刊发了,当看到自己的第一篇文字刊登在报纸上的那刻,难以遏制的激动情绪弥漫开来,并没有觉得自己变得厉害起来,仅仅算是对自己写作的一次认可罢了。
也就是在这次刊发后,我在博客上更新的频率增加了。而自己写了5000多字的小说《结婚七年》也被人搜到出版了合集《那时明月》。当看到自己的文字获得认可,拿着这本书肆意炫耀的时刻里,写作这两个字变得越来越平常了。我想,原来自己也可以凭借自己的手写出人们认可的文字,而这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也是没有意向到的,只是在没人指点的情况下,随意碰撞和摸索罢了,发现新的契机,就会上去写,无论写得好与坏,都尽力而为,做到问心无愧即可。
在博客写作的年代里,有无数的随笔开始在苏州当地报纸上刊发。《苏州日报》、《姑苏晚报》、《城市商报》都曾刊发过我的随笔文字,而当博客鼎盛的年代,苏州新闻网联合出版了一本博客文集《博望苏》,里面收录了自己的多篇文字。只是在博客的年代,我还有着属于那个年代独特的符合,网名。我即以“荷年荷月”的网名行走在博客的岁月里。
五
2008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到一所中外合作高校任辅导员。面对全新的环境,加上工作内容并不满意,我开始在博客上诉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受到作家李敖文风的影响,渐渐地开始了一段与时事评论密切相关的写作生涯。
时事评论的写作,即对当天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点评,迅速形成千字文,有观点有逻辑有文采。那个年段里,正是纸质媒体的黄金时代,也是时事评论迸发的时代。各大报纸和杂志对时事评论的需求量巨大,也导致自己写作的没有停息,甚至还出现了直接点评所在学校和行业内的事情,犯了时事评论的大忌。
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一个新事物,那时并不成熟,尚处于探索阶段,而年少轻狂的自己又在其中工作,看到诸多的弊端和问题,加上时事评论写作的独特优势。于是接二连三地写出了掷地有声的文字,不仅抛出了问题,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比如《中外合作办学路在何方》刊发于《法制日报》、《给中外合作办学看看病》刊发于《大公报》,瞬间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学校领导层的关注。
我的本意是希望中外合作办学会越来越好,但学校领导并不这么认为,总觉得文章的发布引发了舆情危机,对整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是一次阻挠。好的是,那时的我年少轻狂,并不把这些当回事,依旧没有停下时事评论写作的步伐。
从写作到投稿到刊发,全国各个级别的报纸几乎都刊发过我的时事评论文字。中央级别的报纸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等等;省级的报纸像《大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湖北日报》《扬子晚报》《羊城晚报》等等均有自己的时事评论文字见诸报端。一度觉得自己变得牛气起来了,可悲的是,发布了如此多的文章,却并没有收到相同数量的稿费,这些发表,仅仅是满足了自己的夙愿,证明了自己的文字有些市场罢了,但前行的路上,我依旧是且行且珍惜,没有任何停下脚步的意思。
六
在时事评论渐渐式微的时刻,我又开始爱上了豆瓣这个平台。在这里有小组,有发布书评约稿的信息,出版社给邮寄新书,你只要写一篇千字书评刊发豆瓣即可。正是看中这样的交流和活动,我义无返顾地加入其中,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豆瓣上,不断收到出版社的免费图书,撰写着来自内心的书评文字,加上图书公司的推介,书评文字也渐渐登上了各大报纸的版面,这也是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算是意外的收获,也算是对自己文字的认可吧!
书评的写作,有窍门,也有模式,但我总是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诉说,以点睛的书评标题,甚至让书籍作者都十分满意。那是一本《又见炊烟》的散文集,作者是安徽作协副主席许辉。
我阅读完毕后写下的书评标题是“温一轮故乡的明月下酒”,这个标题不仅大获全胜,刊发了无数的报纸,也让许辉本人赞不绝口,他每次去分享该书内容的时候就用了我的书评标题。由此也让我懂得,一个书评好标题就是书评成败的关键,好的书评标题契合作者的内心,差的书评标题离题万丈。
又比如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我用的题目的“乱世浮华一缕情”。因为这本书写的不仅是张爱玲的故事,还有其他女人的故事,用“一缕”很是合适,而胡兰成的时代无疑是乱世,这本书又都是写情的,所以又是浮华的。这就是书评名字的由来,必须是经过我精雕细琢和深思熟虑的,不是随便想想就出来的。
在所有的书评题目中,我特别青睐七个字,或者是八个字,当然也有例外。我觉得,七个字最能体现一个人对于文字的把握程度,当然这些组合必须是百度不到的,否则,题目不能出奇制胜,内容再好也不行。
可以说,这是标题党,但确实很好啊。王东明的《王国维家事》,我用“家事满怀国事忧”;茅于轼的《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我用“给国人的焦虑把把脉”;韩寒的《我所理解的生活》,我用“如你所信地生活”;林文义的《遗事八帖》,我用“深情哪比旧时浓”;虹影的《53种离别》,我用“离别渐远,人生渐长”;庄雅婷的《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我用“莫忘回首前尘路”;戴文采的《今日菖蒲花》,我用“往昔灿若盛时花”。
于是,一边免费读书,一边撰写书评,一边将家中的书房丰盈起来了。如今的书房里,满满装载着的大部分都是通过这样的撰写书评的方式赢得的。这些书,均是免费获得,交换方式只是自己的书评输出,即看到了书,也写了书评,甚至刊发到报纸和杂志上,这何尝不是一件人间美事呢?
七
任何载体的发展都是不可预知的,在时事评论和书评的黄金时代里,人们聚焦于传统媒体,将自己的文字刊发在报纸和杂志上。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侵袭而来,传统媒体渐渐丧失了自己的领地,而我的写作也随之而转移了,从传统媒体转移到网络评论和自媒体写作上来。
网络评论多倾向于正能量和主旋律的弘扬上,尤其以中国文明网为主要阵地,各地的省级新闻网站也曾是主要平台。那时候,对政策的解读占据上风,凡是出台的新政策,都会在QQ群里征集撰写网络评论的人,谁接了就按照规定时间上交稿件。或许是觉得天天写主旋律意义不大,也觉得所写并不是来自我心,也随着网络评论的渐渐式微,自媒体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自媒体的写作,秉承的是流量至上。却带来了另外的担忧。即明明是认真写作的内容,洋洋洒洒几千字下来,最终的阅读量却寥寥无几。此刻,你会在思忖:到底是坚守自己的初心,按照自己的内心去写,还是迎合流量去写自己不愿意写的文字呢?对我来说,还是坚定不移地选择前者。因为我觉得,初心一旦丢失便找不回来了。市场总是变幻莫测的,难道每次变幻都需要迎合吗?今天是流量至上,你迎合了;明天是数量至上,你又迎合了。但你的初心已经不在了,这应该是最为致命的东西了吧!
注册“言立方”的账号,在今日头条、企鹅内容开放平台、搜狐号等多家平台上,只是发布自己多看的电影后的影评,对娱乐事件的观点罢了。自然,这样的经营上也没有太大的流量和粉丝,好的是,写的都是自己想写的,做的都是自己想做的,我想这就够了。尤其是当看着自己的公众号上积攒下来的文字印刷成书的时刻,除了兴奋,别无所求。
在自媒体平台风靡之后,还会有哪些平台来,还会有哪些风口值得写字的人追捧呢?作为一个文字挚爱者,创造的是内容,输出的是文字,传递的却是内心。任何违心之写作,终究不可能长久下去。因为违心可能一时,但终究不可能一世。
如今的我,也会有偶尔的约稿来,这多是以前积攒的朋友资源。无论是小小的网络评论,还是新书的书评,基本上都能够欣然接受。按照对方的意思进行系统化写作,不能够让对方失望而归。我觉得,既然答应对方何时交稿,就无论如何都应该做到,不能够找寻任何借口和托词,否则就是失信于人,如此人家定然不会再次来找寻了吧!
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人负重前行罢了。哪里有什么随随便便成功,不过是傻子一样地坚持不懈罢了。当周围的人鄙夷,你毫无介意;当生活向你开玩笑,你还是初心不改。这就像我如今拿到属于自己的书一样的心情,这纯属20年的意外,又像是对长期写作不止的回赠。
(作者:王传言,山东临朐人,居苏州。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和苏州大学。有100余万字见于纸媒,著有《还你一个乡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