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正烈,炙热的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影散落一地,铜钱般波光粼粼。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新空气,蝉鸣的啁啾如热浪般扑面而来,柏贵喜已经记不清是多少次行走在这片山林中了。
沿途的屋舍、田野忙碌的老农,柏贵喜都记得真切。憨厚的笑容,黝黑的皮肤,头顶着草帽,遇见谁都热情聊上几句,谁能想到这样的柏贵喜是曾经的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系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作为湖北省“第二届最美社科人”,柏贵喜早已把“战场”从青葱校园搬到了漫漫田野。
“柏教授,俩来了啊,这是我们刚刚熟透的烧苞谷,俩快来尝一个。”
“好的,我正好饿着呢。”“巧了,您怎么知道我刚好饿着?”
“俩走了这么远的路肯定饿了,苞谷正好熟了,正好请俩尝尝。”
......
寒来暑往,30多年里,柏贵喜常常利用寒暑假带领学生赴全国各地进行田野调查,足迹曾踏遍五指山、武陵山、十万大山、大小凉山等多个民族地区。父老乡亲们早已将他当成亲人,每年像期盼游子归来般盼望着柏贵喜。
一草一木皆风景,一花一叶总是情,柏贵喜说社科人的根正在田野之间。
没有一朵花,从一开始就是一朵花。30多年前,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柏贵喜即将大学毕业,站到了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虽然对专业内容有深入了解,但是没有任何实地调查经验。
导师的一句话点醒了柏贵喜:“理论研究是为现实服务的,我们的研究就是从书斋走向田野,从书本走向现实。”那年暑假,从来没有做过田野调查的柏贵喜,坐完火车再转汽车,到了鄂西南的山区。从那开始,与乡亲们同吃同住,白天卷起裤腿下地干活,晚上搜集整理资料,伴着牲畜的叫声入睡。
虽然苦乐参半,但是惊奇共存。田野调查不仅解决了柏贵喜在理论上遇到的难题,也让柏贵喜受到了灵魂深处的洗礼。柏贵喜曾拜访过一位60多岁的土家族老人,老人十分热爱传统文化,将土家民歌密密麻麻写在烟盒纸上。事后得知,由于生活窘迫,老人买不起纸张,只能用收集起来的废弃烟盒纸记录古歌。
老人的生活境遇深深刺痛了柏贵喜的心。为什么会有这样富饶的贫困?富饶的文化能否改变文化持有者贫困的生活?为了找到答案,柏贵喜向学校申请报考了民族学专业的研究生,自此走上了民族文化研究的道路,这一走就是30多年。
田野调查是一种文化苦旅,更是一场文化孤旅。柏贵喜已经记不清楚翻越过多少座山,换过多少双鞋,但是由此带来的内心充盈却无可比拟。仅2007年至2012年,柏贵喜就收集整理了一万多件文物和民间故事。
但痛心的是,仍有许多传统文化日渐消亡。柏贵喜亲眼看到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棉后继无人、充满生态智慧的传统吊脚群楼正在快速消失、美轮美奂的彝族漆器苦无销路只能架上蒙尘……从繁华烟火到无名村落,从柴米油盐到织染香墨,田野处处蕴含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都是有灵魂的,如果再不保护和传承,以后连记忆都寻找不到了。
为了征集实物,柏贵喜用脚步丈量田野大地,人托人找线索、湾到湾走访,收集整理了一万多件遗落在人间的珍贵文物遗产。省文旅厅、中南民族大学支持他打造了我国第一家民族学命名的博物馆—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不仅要建馆,还要让它“活”起来,柏贵喜结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立了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争取纳入为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培计划试点单位,同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各类省部级课题200多项,出版学术专著100多部,一个个充满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不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逐渐形成独特的历史标识和时代烙印,展现出民族文化旺盛的生命力。
守一份匠心,多一份思考。柏贵喜认识到文化传承保护不仅是人文情怀、情感纽带,还可以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
为此,柏贵喜与学校积极承担非遗传承人群培训工作,先后举办剪纸、漆器、土家族织棉等3个项目传承人培训班,从一个产业带动一个产业链,从一个人起步到一群人进步。曾经的漆艺班学员王志华将漆艺与木雕“匠心”融入,培养了百余名木雕艺人;剪纸班学员刘秋荣在家乡举办多次剪纸兴趣班,将作品带进了第七届亚洲赏鸟博览会;剪纸班学员徐惠斌成为孝感市雕花剪纸研究所所长,研究所被孝南区设立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剪纸班学员钟聪创作了廉政题材的系列剪纸作品,在当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田野万万里,余生路漫漫,虽衣带渐宽,仍无怨无悔。作为研究生导师,柏贵喜坚持在田野一线教书育人,指导培养文化遗产保护方向博士、硕士生70多名。已年过花甲的他仍扎根于偏远山区,继续在田野中寻找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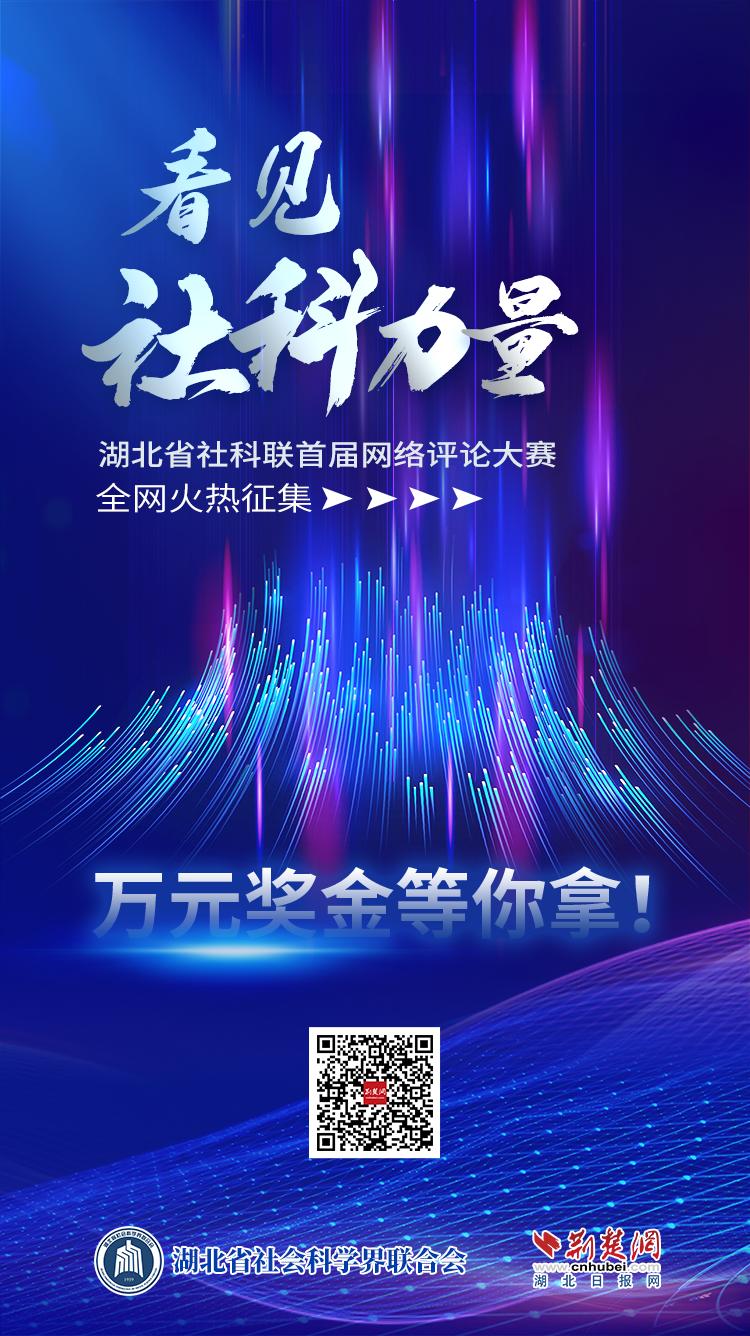
稿源:荆楚网(湖北日报网)
作者:谭金山 (“文安评”网评团队、宜昌市西陵区市场监管局)